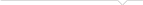■文/本报首席记者 王萌
哈市南岗区学府路1号,绿树掩映下曾是一片安静的厂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还是城市的偏僻角落,宽阔的马路半天见不到一辆车,走出几百米就是农田。哈尔滨电表厂原厂址就坐落于此。
电表厂留给人们的***初印象颇有些神秘。
建国初期,按照***的战略布局,东北是***的重工业基地。人们意识中的大工厂一般都是高大的厂房,机器隆隆。而电表厂却显得安静、整洁,工人上班要穿白大褂,与“标准”的国企形象相去甚远。
然而,建国后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这里一直是我国首屈一指的精密仪表生产基地。这里诞生了我国***台电能表,我国***台解放牌汽车、***轿车的仪表系统,我国***颗人造***精密仪表系统。这里,曾号称“亚洲***大电表厂”。
沧海桑田,如今的学府路1号的老电表厂已经被一片拔地而起的商品房所取代,而在哈平路的经济开发区,新的“电表厂”已正式挂牌。
曾经号称“亚洲***”
哈尔滨电表仪器厂有限公司(原哈尔滨电表仪器厂),始建于1953年,当年是我国“一五”期间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之一。
“我们是65届的大学毕业生,毕业的学校就是原哈电工学院。”有着四十多年厂龄的原电表厂总工程师高福山向记者回忆当年进厂时的情景。
在他进厂前,我国***台自行设计、制造的单项电能计量仪表已于1956年在“哈表”诞生,电表厂已成为我国响当当的精密仪表的生产厂家。
“当年‘哈表’在我国的生产行业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呢?你知道老***轿车吧,它的汽车仪表系统完全都是由哈电表厂制造的,除此之外,我国***台解放牌汽车的汽车仪表系统、***颗人造***的精密仪表系统也出自哈电表厂。在我们***建国后五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哈表’始终处于行业龙头地位。这里,曾号称亚洲***大电表厂。”高福山说。
“‘哈表’不但是我国电工仪表产品的发祥地,亦是我国电工仪表行业标准的制订者,由此可见‘哈表’在我们***的重要性。”高福山说。
据介绍,哈尔滨电表厂是前苏联援建的项目,从一开始,哈电表厂就打上了“苏式”烙印。“许多机器都印着俄文字母,在建厂初期还有前苏联的***进行技术指导,我们的许多生产规范和生产流程都有前苏联工厂的影子。”高福山说。
除了生产上借鉴前苏联之外,在技术输出上也仿效前苏联无私地帮助其他***。“哈表”先后帮助***、罗马尼亚、朝鲜等多个***筹建电工仪器仪表生产基地。在国内,“哈表”为二十个省、市的几十家兄弟电工仪器仪表骨干单位提供技术支持。
生孩子都不用出厂
“前苏联***留给我们的另一个影响,是在企业机构的设置上。”高福山说。企业办社会,几乎是从计划经济走过来的每一个国企必然的布局形态。
掐指一算,原来的“哈表”就能数出从托儿所、小学、中学、技校、大专一直到***等十几个与生产无直接关系的附属部门。
“那时,工人只要是进厂,生活的方方面面工厂几乎就全包了。”高福山说。“小的方面,吃饭、洗澡、理发,工厂有食堂、浴池、理发室。”不但职工中午可以在食堂吃到工作餐,如果条件允许,家里连馒头都不用蒸,可以从厂食堂里面买。大的方面,孩子的教育问题,有学校;家属的生老病死,有工会。我们厂的学校是贯穿了整个教育过程的,***高的可以一直念到大专,毕业后直接进厂就能当技术员。***方面,工厂还有俱乐部,每年到年终搞文艺汇演,夏天的时候开运动会。”1983年进厂的职工高岭对当年的文艺汇演还记忆犹新,“我们厂的文艺人才可多了,一开文艺汇演,厂里面吹拉弹唱的人都有,不用外请人伴奏。”
据介绍,电表厂***也是个有一定规模的***,“能开刀做***”,“女职工怀孕能在这里接生,真正做到了生孩子都不用出厂。”
“企业办社会的目的很大一部分是为职工家属服务,解除职工的后顾之忧,职工家属也确实获益不浅。当年职工家属只要花一角钱就能在俱乐部里看个电影,职工子女***报销一半,许多厂职工的子女都是通过子弟校毕业进入工厂接班的。但是,后来工厂不景气的时候也使许多职工家庭陷入了生活困境。”高福山说。
房子太大没人要
说起电表厂有多大,许多人看到的只是局限于厂区的范围,而实际算上家属区,电表厂的面积非常之惊人。
高福山说:“电表厂职工达到六七千人之多,从哈市南岗区和兴三道街一直到十一道街实际上都是电表厂的家属区,这片家属区被称为‘电表工人村’。除此之外,陶瓷厂后面有一片,哈47中学的后身还有一片。”
对于从计划经济走过来的国企职工来说,分房子可是一件大事。
据高福山介绍,电表厂仿效前苏联的模式,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房子就是三屋一厨、四屋一厨。“那时的房租一个屋也就是两块钱,可是四个屋八块钱,职工觉得浪费,硬是没人住。”高福山笑着说:“***后,厂里没办法只好把一套单元分给几家住。”
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房子的紧张就显出来了,再想找空房子就不容易了。由此,引出许多让人唏嘘的故事。
高福山说:“那时的职工没房住,能分到一套8平方米的房子就感动得直掉眼泪。”高福山那时已经由技术员成长为工厂技术研究所的所长,后来又当上了厂总工程师,他曾多次参加过分房***会。据他介绍,每次分房都要拨出二三十套作为职工的解困房,因为许多住房困难的年轻职工根本就排不上号。
电表厂曾经建过一套“***楼”,本来这些小户型是用于刚结婚的职工作为过度住房,在生孩子之后就搬出去。可是到了住房***紧张的时候,两代同堂或者三代同堂的挤在这样小屋里的大有人在。
“说实在的,那时盖栋房子并不贵,30万元就能盖一栋四层小楼,厂里面的效益也不错,每年六七百万的利润,可是那时的人有了钱都往生产上投,谁也不好意思大兴土木为自己盖几栋住宅楼。”
为了进厂放弃干部指标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哈电表厂不论从生产规模上还是效益上都达到了顶峰。
据高福山介绍,1978年,哈电表厂由部属企业下放到省机械厅。此后的一些年,省机械厅下属企业上交利润总额为1200万元,哈电表厂就占到800万元。
今年49岁的汤泉是新电表厂的党委***。1982年,她进厂时还是一个小姑娘,电表厂技校的毕业生。
进厂之初,不同于一般的工作环境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是在无尘的环境里生产,还要穿白大褂,感觉就像在***里工作一样,那时还很少有工厂是这样的。”汤泉说,初中毕业后,进电表厂成了她就业的***选择,而进电表厂的一个捷径就是考电表厂技校。“当时分数抬得非常高,我要不考技校完全能考进一个不错的高中。”
像汤泉这样进厂的还算是幸运的,据高福山介绍,当时许多人为了能调到电表厂甚至放弃了干部的指标。
当年,电表厂生产的主导产品在市场上也异常抢手。单项电能计量仪表、电工仪器仪表行销***,来自***各地的采买员排队等着提货。“就是我们自己的职工想买一块电度表都得***批条子。”高福山说。
“在民用领域,要说***有名的还得是电表厂出的孔雀相机。”老职工高岭说。
利用自身的精密制造技术,电表厂曾经先后出过孔雀DF-1、DF-2、熊猫、企诺等几种民用相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买孔雀照相机,领完票提货的时候还得排队。”
这种相机不但在国内受到欢迎,甚至受到日本厂商的青睐。曾经有个说法,日本人为了得到孔雀相机的镜头,购买了大批的孔雀相机。高福山告诉记者确有其事,“因为当年我们的相机价格便宜,镜头光学性能特别好,只是外观工艺水平差一些。日本人买走我们的相机后,用我们的镜头配上他们的机身,无形当中提高了他们本身产品的质量。”
电表厂一定能焕发新的生机
“应该说,有几次发展的机遇电表厂没有抓住,导致了厂子的衰落。”说起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工厂的情况,高福山显得有些沉重。
进入市场经济后,老国企观念的落后日益跟不上发展的形势,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发展。恰在这时,城市电网改造和农村电网改造先后进行,“如果那时多投入一点,搞好产品的转型、研发,也不致于错失良机。”
同时,三角债的问题也困扰着电表厂。那时,三角债几乎是每个国企要面对的难题,要钱、***、以账抵账是厂***大会小会不断强调的中心工作之一,以致于当时还身为一名普通工人的高岭学会了一个新词“抹账”。
高福山说,由于三角债的影响,电表厂的资金流动周转极为缓慢,“国外的同类企业资金周转一次用60天,而我们要400天,有时达到500天,还拿什么和人家竞争?”
企业发展出现困境,而计划经济时代留给企业的附属社会功能成为了沉重的负担。高福山说:“现在想起来都是笑话,当年花大力气办起来的学校现在想推都推不出去,原来的子弟小学推给现在的主管部门,我们甚至倒找了30万。”
企业办社会留下的附属部分剥离之后,电表厂又对下属的十几个分厂进行了剥离。从此,原有六七千人的厂区冷清了许多,俱乐部里不再上演电影,厂冰球队、篮球队解散,曾经让职工回忆起来倍感温馨的文艺汇演也成为了绝唱。
然而,企业的下滑并没有停止,直到2004年,电表厂进入了***期。
“好在电表厂没有一蹶不振。”汤泉说,2005年,哈电表厂终于触底反弹。当年,上海人民企业集团注资对该厂进行***改制,并在哈市开发区建起了如今占地5.4万平方米的“哈表高新工业园”。新成立的哈尔滨电表仪器厂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金灵丰说:“哈电表厂曾是中国精密制造的一面旗帜,我们不但要让这个品牌继续在国内市场生存下去,而且还要把它推向世界。”
而对于老电表厂的员工来说,仍是“故土难离”。工厂搬迁之后,老厂区成了他们***常挂念的地方。“搬家那天,不少退休的老职工都来了,大家争着在厂区留影,眼泪止不住在眼眶里打转。”汤泉说。
据介绍,哈尔滨电表厂实现彻底改制后,哈表集团公司于7月1日正式挂牌成立。新的厂区为电表厂带来了全新的面貌,汤泉说:“哈表人振兴企业的精神没有变,在市场经济中,哈电表厂一定能焕发新的生机。”(本版图片均为资料片)